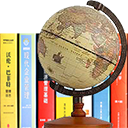生活是欲望、奋斗和期盼,但我们为何无聊?
01
无聊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
一直与我们同在
你的目光离开洗碗池里的盘子,望向窗外的后院。一股烦躁涌上心头。你想做点什么,做什么都行……

但到底是什么呢?你一直心烦意乱,此刻刚刚注意到你的狗。
它是一只澳大利亚牧羊犬,灰蓝色斑点布满全身,深棕色的斑纹勾勒出一张警觉的脸。它习惯奔跑着将羊群或牛群围起来,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技能,但看起来它毫不费力。
你每天遛狗两次,老实说,这已经是夸张的估计了。但是,对它这个活泼的小生物来讲还远远不够。它需要宽敞的空间,需要活动,需要一个目标和一份工作。这跟你没有什么分别。
这会儿,没有羊群需要它赶进木栏,它只顾着绕着你的草坪全速奔跑,画出一道道宽阔的圆弧。
通常,这会让你的嘴角上扬。这条狗一心追着自己的尾巴,偶尔会抓到它,这看起来很有趣。但也很没意义,你意识到。
就在这时,它停止了转圈,喘着粗气,捕捉到你脸上的笑意。它忧郁的表情让你的笑容慢慢凝固。
你呆滞的神情让它察觉到,你没有解救它的打算。你不会做任何事来将它从烦闷中拯救出来。于是,一圈圈没有尽头、毫无意义的奔跑又开始了。
如果你的狗也会觉得无聊,那你又有什么希望能解决自己的莫名烦躁呢?
它很无聊,你知道的,它也知道。
戴洛克爵士:“亲爱的,外面还在下雨吗?”
戴洛克夫人:“是的,亲爱的。我都快烦死了。我烦死这个地方了。烦死我的生活了。烦死我自己了。”
这段对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的鲜活描述来自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的电视改编版。在此书中,狄更斯第一次引入了无聊(boredom)一词。
虽然在此书之前,英语里已经有无聊的人(bore)这个词,法语里也早有ennui一词来描述一种倦怠的感觉,不过无聊一词直到19世纪后期才被广泛运用在英语中。但是,没有概括这种体验的词语,不代表无聊就不存在。
无聊,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与我们同在。
它是我们的生物性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生物性是由漫长的演化塑造而成的。无聊有着复杂又迷人的社会、哲学、文学、美学和神学历史——这一历史太过复杂,在此无法全部涵括。但是,要真正了解无聊、定义无聊,我们必须从某处着手。
02
无聊源于对日常生活缺乏激情
彼得·图希在他精彩的著作《无聊:一部生动的历史》中,将无聊的起源追溯至古代。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也许是第一个描写无聊的人。他有感于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将无聊与恶心和厌恶联系到一起:
这样过日子有多久了?当然了,我会困,会睡,会吃,会渴,会冷,会热。这样的日子是否没有尽头?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日夜交替,四季更迭。过去的会再次到来。我没有做什么新的事,也没有看见什么新的东西。有时,这让我感到恶心。在很多人眼中,生活并不痛苦,但很空虚。
他的悲叹听起来并不过时,
塞内加抱怨日复一日的重复,显然,让我们想到那句“太阳底下无新事”。
有人可能会说,《圣经·传道书》对单调日子的哀叹要比塞内加的描述更早一些。

在概述了财富和名誉带来的辉煌之后,《传道书》的叙述者说道:“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无论是塞内加还是《传道书》,两种怨语都强调了无聊的两层内涵。其一,无聊是一种负向体验;其二,它让你觉得没有意义可言,让生活看起来很空虚。
图希甚至告诉我们,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一个村庄纪念了一位官员,因为他神奇地将人们从不可忍耐的无聊中解救了出来!
无聊源于对日常生活缺乏激情
,这种情绪在中世纪也赫然可见。
一些学者认为,现如今我们所称、所理解的无聊源自拉丁语中的acedia,该词指的是对维持禁欲生活的灵修缺乏热情——一种精神上的疲倦和怠惰,以至于葬礼等仪式也失去其意义。
既无精打采,又焦躁不安。
无休止地重复每天的例行公事,这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正午恶魔”,它在隐居的僧侣们中间催生出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塞内加和僧侣们不仅指出了单调和无目的所具有的压迫性本质,而且向我们展示出,无聊早已与我们同在,远早于狄更斯对它做出的描述。
直到19世纪中晚期,对无聊的心理学探讨才开始出现。
正如我们在心理学历史中经常看到的那样,是德国人打响了第一枪。当时以人类学研究而闻名的特奥多·魏茨与哲学家特奥多·利普斯研究了德国人所说的“Langeweile”(字面意思是“半晌”)。
对魏茨来说,无聊与意识的流动有关。
当一个念头引发下一个念头,我们就会对这缕思绪的终点有所期待。当这种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时,无聊便产生了,意识的流动因此出现了断点——思绪脱轨了。
无聊的产生源于一种冲突
利普斯则认为,,即我们渴望“强烈的心理活动”,却又无法受到刺激。
英语世界的心理学开拓者、博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对无聊也有类似的思考。高尔顿研究了被中世纪僧侣称作“正午恶魔”的焦躁的概念。
高尔顿不断寻找衡量人及其行为的方法,他记录了在一场枯燥的科学讲座中坐立难安、左右摇晃的观众——这是烦躁和无聊的明显表现。
这种乏味和随之而来的无聊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信息在数量上增长,却以质量为代价。
在20世纪初的一次演讲中,詹姆斯哀叹道:“一种无可救药的乏味即将席卷这个世界。”对詹姆斯来说,
它们都强调了无聊的核心:这是我们头脑空空的信号。
这些对于无聊的早期探讨都暗示了一种不适感,即想要投入令人满足的活动,却又无能为力。
03
它是永恒的,意味着一种空虚
詹姆斯所谓“无可救药的乏味”、塞内加对千篇一律带来的恶心感的哀叹都指出了无聊这一体验的关键要素——一种事情缺少意义的感觉。
意识到生活的荒诞,会使人产生焦虑之感,存在主义哲学家对此进行了探究,他们也因此成为最早对意义在无聊中的作用进行系统阐释的学者之一。
表现为我们对于欲望的具身体验
存在主义的悲观先驱亚瑟·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根本现实最直接地。换句话说,生活是欲望、奋斗和期盼。
如果人生是无休止的渴望,那么我们怀有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满足;一个欲望实现了,另一个欲望又出现了,欲望本身一直存在。幸福——从欲望中解脱的片刻——永远是即将降临。
幸福一旦到来,新的欲望将立刻现身。根据叔本华的说法,我们注定要长久地受苦,因为心中的欲望如流水般永不停歇。两个悲惨的选项摆在我们面前:欲望未了的痛苦,或是无欲无求的无聊。

索伦·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另一位先驱,他也将无聊同寻找或领会意义的奋斗联系起来。当无法充分地领会意义时,我们会觉得自己贫乏且无能。
在著作《非此即彼》中,克尔凯郭尔通过奉行享乐主义的叙述者之口说道:“无聊根植于虚无,虚无贯穿于存在;它带来无限的眩晕,就像凝视无限的深渊一般。”
对克尔凯郭尔观点的一种解读是,之所以“无聊是万恶之源”,恰恰因为我们寻求一切方法来避免无聊。
躲避无聊实际上是在加强它的束缚
。如果我们没有那么渴望逃离无聊,它会将我们引向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人生目标的热切追求将成为我们的向导。
事实上,《非此即彼》下卷坚称,当我们放弃享乐主义,过一种更加合乎道德的生活时,无聊也将不再那么令人苦恼。
在试图定义无聊时,最后一个不得不提的存在主义者是马丁·海德格尔。首先,海德格尔让我们想象自己坐在一个火车站,等待一辆晚点两个小时的列车。
巡视这个火车站只能提供最肤浅的娱乐。我们有书或者可以打电话,但也只能带来片刻的消遣,很快我们就需要新的对象来转移注意力,消磨时间。
海德格尔把这种情境称作浅层的无聊,指向一个还没有到来的外部对象,或一个还没有发生的外部事件。换言之,时间变得漫长。
接着,海德格尔让我们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社交场合,某个愉快、惬意的聚会,也许是庆祝某位同事退休的聚会。
我们谈论时事,交换彼此子女的最新成就或者小缺点。如果在加拿大,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讨论天气。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意识到,整个时光虽然足够欢乐,但毫无意义!
也许我们颇为投入,但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投入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我们感觉自己的时间被浪费了。
与这种无聊相伴的活动并不会和一个具体的对象或事件(例如等待一列火车)直接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无聊的第三个层面,也是对海德格尔来说最重要的一层——深度无聊。
它是永恒的,意味着一种空虚。在这种空虚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的恐怖之处。
这种无聊不指向某一对象,也没有明确的触发点。
因此,纵观历史,无聊一直与庸常生活相联系(塞内加所言的“日夜交替”)。由于没有一件事能保证让我们此刻或未来得到满足,我们每日的奋斗似乎空无意义。
这就是无聊的讽刺之处。一方面,它凸显了存在本身的无意义;另一方面,它促使我们永不停歇地追求新鲜和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希望能够满足我们的东西。
无聊看作应对焦虑的一种解药。
存在主义者把无聊视作缺乏意义引发的一种问题,精神分析学家则把

无聊是“一种悬而未决的期待状态,
英国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写道,事情开始了,却又什么都没发生;一种弥漫开来的焦虑不安,它包含着最荒唐、最矛盾的祈求,祈求一种欲望”。
每当我们被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所威胁,无聊便会产生。
这段文字是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一句话的改写:“无聊——一种对欲望的渴望。”所以,根据精神分析学家的看法,
人生意义的缺失和内心深处的冲突,这些似乎都是人类独有的问题。
20世纪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艾里希·弗洛姆有句名言:“人是唯一会感到无聊的动物。”弗洛姆错了吗?无聊真的是人类特有的体验吗?看到你的猫追着激光笔跑,很难想象她会体验到存在主义忧虑,或者焦虑于不被接受的欲望。
04
必须拥有自主决定权,
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到世界中
不难相信,动物也会投入游戏。无论是嬉戏打闹的虎崽或狮崽,还是滑下泥泞的斜坡、冲进象群的象宝宝,抑或是用尾鳍把海狮高高抛起然后驱走的虎鲸,似乎显而易见,动物们喜欢玩耍。
早期关于玩耍的功能的理论认为,玩耍是为了培养幼崽成年后必备的技能,或者是一种重要的社交纽带。这些说法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动物幼崽之所以玩耍,并不仅仅是为了长成更凶猛的狩猎者,或是为了拥有更多的朋友。
有关动物玩耍行为的最新理论认为,玩耍可以带来短期的利益,对人类来说亦是如此——玩耍能够减轻压力。

如果我们承认动物会玩耍(也许出于和人类一样的原因),那么,我们为何不能相信动物也拥有其他我们曾认为是人类独有的体验呢?换句话说,动物会感到无聊吗?
如果玩耍能够帮助动物应对压力,那么,当它们被阻止投入它们通常会选择的行为(玩耍或其他)时,无聊也许就会产生。
贫乏的生长环境对动物会产生有害影响,包括抗压能力低下、适应性差和大脑发育迟缓。反之亦然——丰富的成长环境有利于动物的脑神经发育。
和本书主题尤其相关的是,有些学者认为在贫乏的环境下长大的动物有类似于无聊的行为表现。
弗朗索瓦·威梅尔斯菲尔德(Françoise Wemelsfelder)是苏格兰农业学院的科学家,他始终认为,动物也会感到无聊。在他看来,圈养动物所处的封闭空间是罪魁祸首。
有限的空间显然也使得动物可以选择的行为变得极为有限。它们只剩下一些模式化的行为可做,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不能体现动物在野外生活时的通常所为。
正如我们将在整本书中所讨论的那样,作为人,我们感到无聊时,实际上同样是面临对我们的能动性的挑战,换句话说,我们感到主宰自己生活的能力受到挑战,或某种形式的限制。
但我们怎么确定动物是真的体验到了无聊,而不是别的东西呢?
圭尔夫大学的丽贝卡·马尔(Rebecca Meagher)和乔治娅·梅森(Georgia Mason)进行了一项研究,探究如何区分人工饲养的黑水貂的几种情绪——快感缺乏、冷漠和无聊。
快感缺乏的人感受不到愉悦,冷漠的人漠不关心,无聊的人则渴望投入什么。
快感缺乏是指无法体会到快乐,在人类身上,它与抑郁症有联系。冷漠被认为有别于无聊,因为它表现为缺乏兴趣,且无意改变现状。相反,无聊的特征则是一种想要做些什么的强烈愿望。换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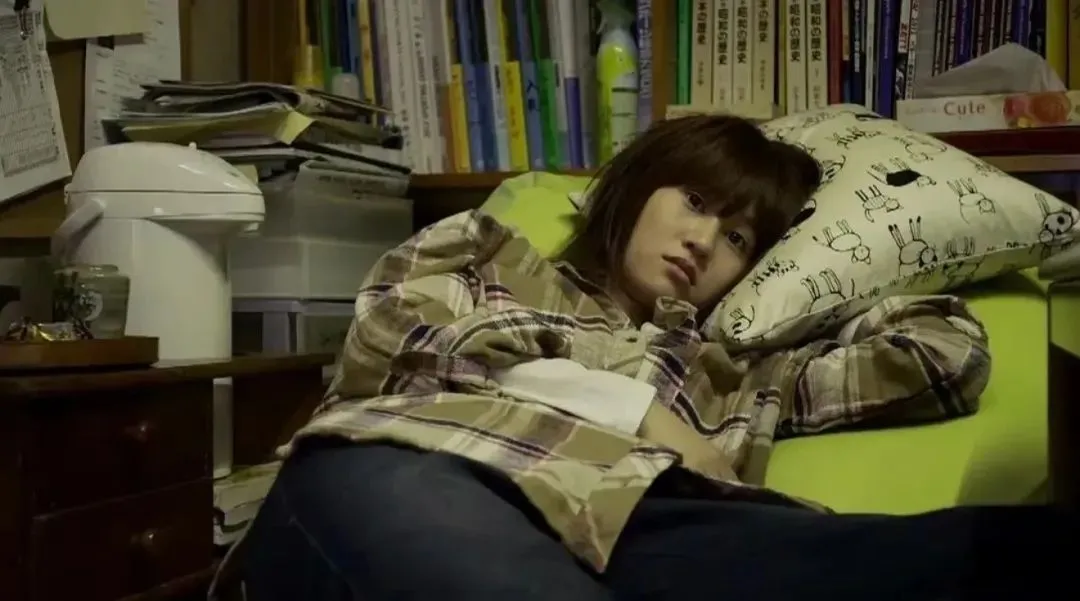
当然,问题在于,我们没法儿让一只动物直接告诉我们它什么时候觉得无聊(或者冷漠、快感缺乏)。但是我们可以研究动物面对新刺激时的行为,这正是丽贝卡·马尔和乔治娅·梅森所做的。
马尔和梅森测试了两组水貂,一组饲养在条件贫乏的笼子里,另一组则饲养在条件丰富的笼子里,允许进行更为多样和探索性的活动。
研究人员分别给两组水貂展示了三类新刺激——厌恶刺激(捕食者的气味)、奖励刺激(移动的牙刷,相当于猫咪眼中的激光笔),以及模糊刺激(塑料瓶),同时记录了水貂接触新刺激的时间、时长和次数。
这个实验背后的逻辑是,冷漠的动物会逐渐失去对所有新刺激的兴趣。相反,快感缺乏的动物只会对奖励刺激失去兴趣,因为此类动物无法感到快乐,所以不会主动靠近通常来说能够引起愉悦或积极反馈的物体。
对无聊的动物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研究人员认为,无聊的动物会无差别地接触所有刺激。换言之,如果一只生活在条件贫乏的笼子里的水貂感到无聊,那么任何新刺激都可以满足这只水貂参与世界的需要。
研究人员观察了两组水貂接触的刺激类型,以及看到刺激物展示后水貂的反应速度有多快。条件贫乏的笼子里的水貂会更快地接触所有类型的刺激——包括捕食者的气味!
这么看来,这些水貂并非抑郁或者兴趣缺失,它们极为渴望刺激,这显然是无聊的表现。
研究人员也观察了补偿性行为,即水貂吃了多少食物。条件贫乏的笼子里的水貂比条件丰富的笼子里的水貂吃得更多。人类也会通过吃来弥补无聊的空虚。
即使我们不用无聊这个词来描绘水貂,这项研究也表明,饲养在贫乏环境中的动物会对新的行为或刺激非常敏感。
当然,所有这些结论仅适用于圈养动物。野生动物也会感到无聊吗?
也许会,但这种无聊只会持续非常短的时间。在没有限制的自然环境下,动物能自由决定它们的行动。而圈养动物注定只能过单调的生活,它们被囚禁着,无法体验在野外通常会进行的一切自由活动。
我们必须拥有自主决定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到世界中,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自由选择。
所以,对人类和动物来说,重点都在于,仅仅是眼花缭乱的选择和激励并不够。
实际上,过多的选择和持续的刺激都会超出我们的控制,这种感觉一点都不舒服,更像是焦虑,甚至是狂躁。选择是关键的。
要做出选择,我们必须认定一项活动比另一项更重要或更能使我们满足。而研究表明,动物与人类一样,也会区分不同活动的重要程度。如果它们更看重表达自我的自由,那么它们必将被无聊所困。
是一种技能和环境的不匹配
所以,圈养动物的无聊让我们看到的,它们本可以在野外自由施展自己的生存技能,而现在却被环境所限制。,动物和人类都是如此。

本文摘编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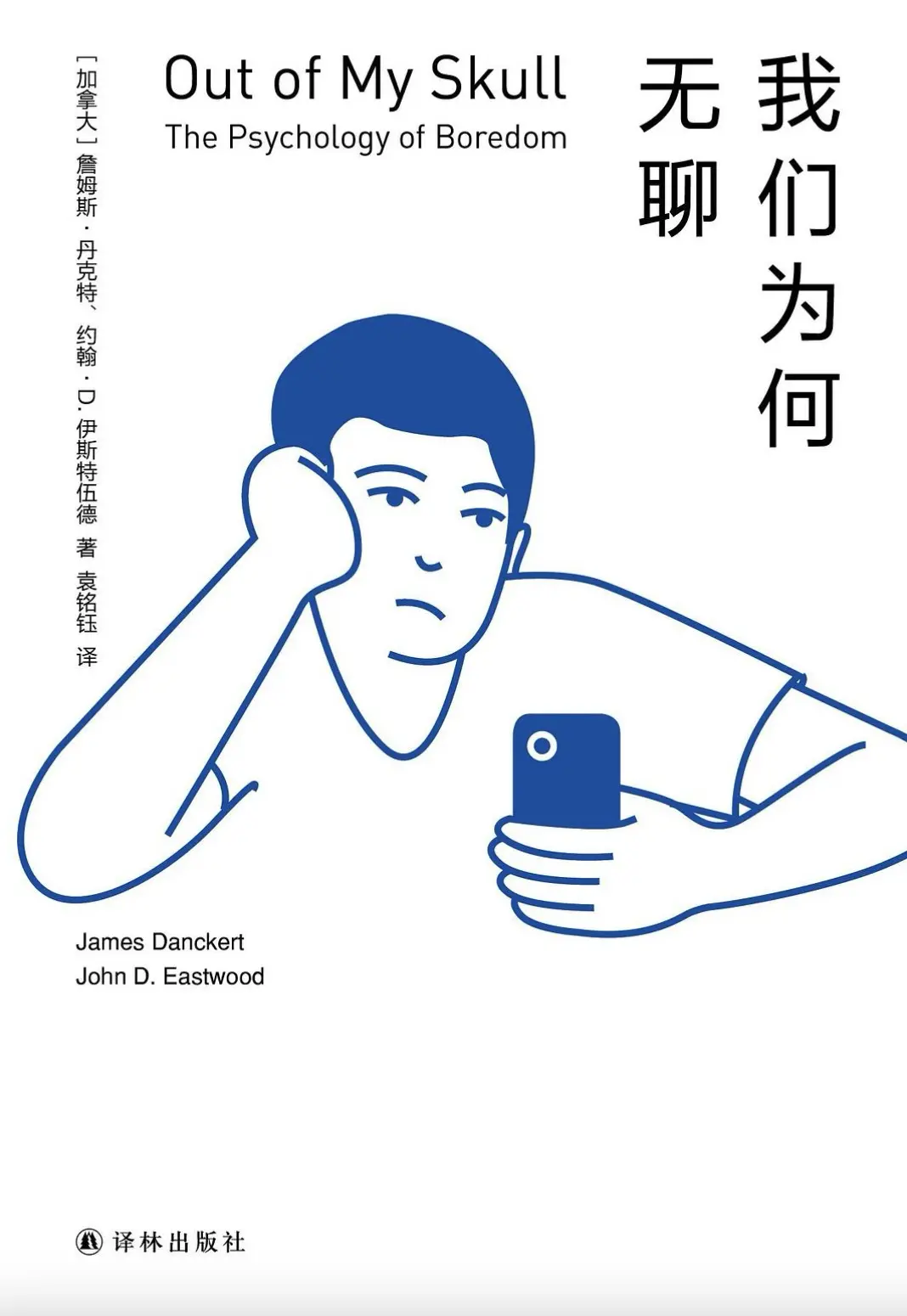
《我们为何无聊》
作者: [加]詹姆斯·丹克特 / [加]约翰·D.伊斯特伍德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袁铭钰
出版年: 2022-2
来源:凤凰网